这一日白瑞起得很早,不到卯正便已梳洗完毕。他穿好昨晚浆挺的长衫,理好头发,便出了房门。走至西角门,从一大把钥匙里拿了一把开了锁,抬头看见有四个婆子早等在那里。带头的那个慈眉善目,赔笑着叫了声:“大总管早。”白瑞点了点头,瞧见最后面的那个婆子脸生,便皱皱眉,问道:“张保家的呢?”那为首的婆子赶忙答道:“张保家的昨儿病了,烧了一晚上,今早起来人还虚着,我怕误了您的事,就找了吴嫂子来。”白瑞说:“白府可不是生人随便进的。”那婆子又道:“她是我表亲,前年白老爷摆寿酒的时候她进大厨房当过差,伺候大夫人的应嬷嬷认得她。”白瑞想了想,便问:“做事得力吗?”那婆子忙笑道:“得力,她力气大,做事又干净利索。”白瑞恩了一声,又微微笑道:“我是看在您老面上,这几年来是稳妥的人,所以相信你带来的人,这儿不比外头,一言一行都是有规矩的,须谨慎的好。”那婆子看了一眼后面,最后一个婆子赶紧站出来说道:“大总管说的是,奴才一定安守本分,决不违规越礼。”白瑞便叫这四个人进来,带着向东从外宅走到后院大厨房交给那里的总管杨喜,又对杨喜吩咐了几句,杨喜一一点头。正抬脚要走,忽又想起一事,转身回来叫住杨喜道:“上回你拿来的菜单里有一道是叫凤抬头的。”杨喜道是,又说:“说是凤,其实是上好的田鸡。”白瑞便说:“换了吧,或改个名。”杨喜抓抓后脑:“这是为什么?名字不都是几位大师傅取的,为了讨彩头的?”白瑞笑道:“怪不得前些天叫大太太训了一顿,你做事就是不会用脑子,也不打听打听这位新夫人的闺名,就胡乱往菜上扣名字,以后都不知怎么死的。”杨喜拍了拍脑袋瓜:“多谢大总管提点,您老就是见过世面。”忙打着秋千送出来。杨喜回到厨房,笑盈盈对这那婆子说:“于奶奶,好久不见,我老想着你弄的八宝饭,今儿可有口福了。”那于婆子啐了一口,笑骂道:“狗崽子,几日不见嘴越发贫了,你们这里什么没有,倒叫你想着我破灶子上的饭!”她对其他几个婆子派好了事,又说:“这府上好久没办喜事了,这新夫人一进府必散赏钱,到时候又便宜了你们这些猴孙!”杨喜撅撅嘴道:“得了吧,咱们能赏到些什么,这层层派下来的顶多是牛身上的毛,上回四小姐过生日,不但没赏还讨了顿骂。”于婆子道:“这又是为什么?”杨喜道:“我的好奶奶,您是没亲身经历过,哪能知道服侍这一大家子夫人小姐的难处。”于婆子一笑,又说:“这话说回来,今天进门的是老爷的第七位夫人了吧。”杨喜哼了一生,道:“可不是,一个个往府里娶,弄得鸡飞狗跳的,连大夫人都暗地里抱怨呢!”于婆子忙道:“罢了,你的嘴就是会乱说,我一路看这排场,可见老爷对这新夫人很上心。”杨喜嘻嘻笑道:“那当然,要是我也能得个名满省城的大美人作老婆,必也张红挂绿用八抬大轿子迎进来。”于婆子啐道:“就你这猴样,不好好训一顿,还给你找媳妇儿。”彼时厨房里的人多了起来,二人便各自去做事去了。 这里白瑞离了厨房,便沿外宅走回,到了垂花门前就瞧见几个婆子在喷水扫地。白瑞不敢贸然进去,只在门口等着。一盏茶的工夫后天已经大亮了,只见从正院里走出个嬷嬷,衣着体面,发暨整洁,迎着白瑞走过来,微微笑道:“大总管早。”白瑞亦笑回:“嬷嬷早,老爷起来了?”那嬷嬷道:“已经起了,梳洗了去东偏厅用早饭呢,总管这边请吧。”引着白瑞经一边的抄手走廊向东,穿过一扇仪门,又走了半盏茶工夫这才进了偏厅,轻轻带了门出去了。白令璩已用完了早饭,正站在里间让两个丫头服侍他穿朝服,看见白瑞来了,便问:“今儿的事都妥当了吗?”白瑞因瞧见有丫头在里面,料有女眷,便只站在外面房间,口中答道:“都安排好了,未時二刻七姨太在殷家上轿,申時初进西大门,然后行礼,之后老爷便去前面见客,晚宴一到酉時就开始。”白令璩问:“二少爷起了吗?”白瑞道:“奴才从前院过来的时候还早,没遇见伺候二少爷的人。”白令璩道:“告诉外面的人,叫二少爷起了就往外院去,我有话吩咐。”刚刚说好,里面厢房里就走出个妇人,笑道:“才刚月容来回,二爷已经在前头等着了,老爷放心。”白瑞垂首,恭敬地叫了声:“三姨太早。”那三姨太李氏高佻身材,凤眼修眉,虽年近四旬却不露疲态,穿着大红洋缎窄裉袄,外罩白毛银鼠褂,身下是翡翠色的绉裙,浑然间的风韵尤存。白令璩这时已穿戴整齐,他的身体原本挺拔,过了四十之后已微微发福,不过叫剪裁合身的朝服遮去了些短处,领子在脖子处扣得很紧,使得脖子直直得立着,他十几年来已习惯了这种姿势,叫人看上去十分庄严。他的嘴角微微下弯,不轻易露出笑脸,一双眼睛不大,但透着威严和果断,含威而不露。这边李氏边吃茶边对他说:“老爷,澈儿已经长大了,前儿宫里头的敏公公还夸他呢,皇家的差事他都误不了,更何况迎亲这种事。”白令璩道:“给你染料就开染坊,夸他是宫里的人是给咱们白家面子,他是有点能耐,但要当好宫里的差使还要多多历练,回头敏公公再来,你别轻佻失了分寸。”李氏委屈道:“老爷也太小瞧我了,跟你这些年,厉害的本事虽不会,分寸我还是知道的,澈儿是我教出来的,自然也同我一样,虽然入不了老爷的眼,但也决计不会让白家丢脸。”白令璩手中拿着几本折子细看,不语。李氏又说:“自从老爷定下了殷家的亲事,我哪天不是随着大夫人忙里忙外,筹划应对,澈儿那里我也嘱咐了好几回,就恐出些纰漏,反正我怎么小心就是顺不了老爷的心,正是俗话说的好:‘只见新人笑,哪闻旧人哭。’”说到这里已有几分哽咽。白令璩抬头,皱眉道:“我不过白嘱咐嘱咐,哪来那么多话!”李氏不答,只呜咽几声,倒显得越发可怜。白令璩回头见白瑞早回避了,只得走上前来安慰几句,李氏又哭了几声方才止住,勉强笑道:“老爷快上朝去吧,若耗在这里误了时辰,我的罪过就真的大了。”白令璩一笑,这才出门。 白瑞瞧见白令璩出了门就紧紧跟着,他让后面的人慢行,见四下安静,就轻轻在白令璩耳边道:“老爷,昨儿在徽县边上的江里捞起了具尸首,赵锦堂来递话说模样很像黄津的儿子。”白令璩沉吟一下,道:“叫姓赵的去查清楚,如真是黄津的儿子,叫他直接递折子给圣驾,不必再来回我。”又走了几步,问:“韩广善的宅子还有人去吗?”白瑞道:“早没了,大白条贴在大门上,谁还会进去。”白令璩微微冷笑:“只怕有人还不死心,你没瞧见斩韩广善那天城门口那些守军的神色吗?百姓也跟着起哄,姓韩的还真是广结善缘啊。”白瑞道:“只可惜皇上仁慈,放过了他两个小儿子。”白令璩道:“那还不是叫陈公和屈大头力包,哼!那两个老家伙就会在皇上面前倚老卖老,你给我盯好了韩家的那两个小鬼,别叫他们又兴风作浪。”白瑞面有难色,不得不回道:“老爷,韩子巽和韩子离两天前已经失了踪影了。”白令璩脸色一沉,白瑞忙道:“小的已经加派人手去找了。”白令璩喝道:“当时怎么不回?”白瑞道:“小的看这两天老爷欢喜,合府又办着喜事,所以不敢惊动,只叫人暗地里去找,本想着这几天会有消息,谁晓得……”白令璩接道:“谁晓得就是找不到,你当他们一大家子人会平白无故消失吗?朝中暗施援手的人会少吗?韩子巽那么精明,你会是他的对手吗?你什么时候学会自作主张了?”白瑞身上渐渐起了一层汗,只得道:“是小的失职,要是找不回来,小的甘愿受罚。”白令璩冷笑道:“找回来做什么?皇上既然开口放过他们,我们还能拿着刀子向上赶吗?你去留心三皇子的人,如果他和韩家有往来就立刻来报。”白瑞道:“小的已经派出人了,还把内廷侍卫焦正换了,怕人疑心。”白令璩笑道:“总算你还有得力的时候。”又道:“还有八皇子,也派人留意。”白瑞道:“是。”二人已走进大门,大门上挂着大红色的缎子,风一吹过,盈盈地动着,门上贴着两个大红喜字,此时太阳已升高,阳光射在新漆过的大门上,照得那两个喜字分外扎眼,门下站着个年轻公子,身材颀长,面容清秀,神情祥和,见到白令璩,恭敬地叫了声:“父亲。”随后又微笑道:“白叔早。”白令璩打量了下他,嘱咐道:“见了殷家的长辈要有礼貌,礼数上的事跟着你六叔。”白澈笑道:“知道了,母亲都叮咛过了。”白令璩笑道:“还提你母亲,一大早就属她最会闹事,我也不敢多教训你,你先去见了你母亲,再找你六叔去,不许吃酒,到了时辰就出发。”白澈一一答应了便去了。这边白令璩出了大门,早已有轿子等在那里,他回头望了一眼大门,止步不动,白瑞度量着,轻轻说道:“老爷,你不必为韩家的事挂心,现在连殷老都投靠你,他还是韩广善的妹夫呢,可见他们是气数已尽,那两个小的虽然能干,但都是毛头小子,气候未成,况且圣上对韩家已心怀芥蒂,再次起用恐怕是遥遥无期。”白令璩沉吟不语,转身上轿去了。 第2章 皇帝正在漫不经心地抓着围棋子,另一只手端着茶杯,偶尔会有几声咳嗽。皇帝圣体欠安已有一段日子了,他病势虽不凶猛,但连绵不断且伴有低热,叫群医惶惶不安了好一阵子。倒是他自己不以为然,作息依旧,只是饮食清淡了些,这十几天倒也渐渐好了。下朝后,他把白令璩传到了上书房继续询问一些病时拖延下来的折子,其中不少是如何处置韩黄余党的,皇帝看了会儿便露出疲倦之态,彼时八皇子也在侧,皇帝便问他的意见,八皇子笑道:“父皇好偏心,遇到惩处杀伐之事便问我,施恩受惠之事却是国舅出面,儿子的脸都叫您涂黑了。”皇帝笑了出来,对着白令璩说:“听听,这个儿子长大了,懂得跟朕计较了。”白令璩亦笑道:“这哪里是和皇上您计较,只怕是和臣在争差事呢。”八皇子笑道:“谁叫国舅爷拦的件件都是美差呢,上回南下巡视河堤,我求了父皇两次都没准,倒叫您给检去了。”皇帝道:“你才多大?你当这是游山玩水吗?这其中的权衡度量,运筹规划,若没有几十年的经验和资历去担当,河防早塌了十次了,不知轻重,你当你国舅和你一样,没事就出宫去养鸟玩棋吗?”白令璩忙笑道:“八皇子才十六岁,好动在所难免,再说臣常有听说国子监的师傅赞八皇子的功课,说其风韵灵动,是皇上望子心切了。”皇帝笑道:“不过是投机取巧,朕看躲懒他倒排第一。”又转过头去对八皇子道:“韩广善那一伙余下的琐事你留着心,从明天起让白公帮你,朕不把你的脸全摸黑了,就只摸一半吧。”八皇子笑道:“儿臣谢父皇体谅。”皇帝又对白令璩道:“你替朕看着他,不许他偷懒。”白令璩忙道是。八皇子道:“父皇,咱们别扣着国舅了,他家里正办喜事呢,您就放他走吧。”皇帝仿佛忽然想起,笑道:“朕倒忘了,听说新姨太才貌双全,白公你好福气。”白令璩笑道:“流言蜚语而已,岂敢让皇上谬赞。”皇帝叫了太监:“把前几日进贡的那柄翡翠如意送到白府,算是朕的贺礼。”白令璩忙道:“区区一贱妾,岂敢受皇上如此大礼?”皇帝笑道:“罢了,误了你当新郎倌,算是朕的赔礼吧。”白令璩忙道几声不敢,又谢了恩方才请退。 这日未时刚过,白府中已热闹非凡。本来白令璩纳妾并不需大张旗鼓,只是韩黄一案让朝中诸事又重归白府掌控,再加之陈公已老且病,殷越正倒戈,这次白殷两家的婚事倒像是白令璩重掌大权的庆会,朝中官员大都随波逐流,就算不亲到也派人送来贺礼,也有几个刚烈的不惟所动,但也只是敢怒不敢言。此时大门口已聚集了许多人,有官员坐轿前来在门口寒暄的,有百姓围观的,有小厮维持秩序的,还有许多孩童围着炮仗乱跑的,沸沸扬扬,喧嚣之声不绝于耳。想来这国舅府平日大门紧闭,平常人只得远远瞻仰,所以这日围观的人异常多,人群中有个叫马婆子的,也带着自个儿的孙女来凑热闹。那个小孙女才八九岁的摸样,正蹦蹦跳跳的喊着:“奶奶,新娘子怎么还不来啊?”马婆子笑道:“别急,就来了。”另一边还站着个老人,对着马婆子道:“想那殷小姐五六岁的时候,还叫老生看过面相呢,那时我就给了四个字:大富大贵。”马婆子笑啐道:“又给你瞧过!凡是皇孙贵胄你都瞧过!越老越不要脸。”那老人自抱起那个女孩子,笑道:“小凤儿,瞧你的摸样也不必那殷小姐差,等再过几年也进这白府,你可道好?”那女孩道:“奶奶说新娘子和我的名字一样,模样也和我一样吗?”老人笑道:“一样一样,等你这小凤儿长大了,也一样的如花似玉,一样嫁进国舅府。”马婆子骂道:“你作死!我好好的闺女干吗给人去做小老婆。”说着就要去抱那孩子,小凤儿却自己脚一蹬下来了,偏生人太多,一个趑趄没站稳,踩到了后面的人,马婆子忙向后一瞧,只见一穿着黑衣的少年,长挺玉立,面容英俊,他被人踩了却浑然不觉,只是一双亮目正凶狠地盯着前方。恰巧这时新人的轿子已到了西大门,一时间锣鼓巡天,马婆子就注意那边去了。因为站得远,就只见一个娉婷的红色身影被人搀着下了轿,就只在门口停了一会,新娘子似想回头,但整个身影只一顿,就叫门口的婆子媳妇欢天喜地地搀进去了。马婆子看了这景却微微叹了口气,道:“这候门似海,这样嫁进去也未必是福气。”正感叹间,觉得身后有人在拉扯,回头瞧见却是刚才那黑衣少年身边有多了个老人,那老人似是个仆人,正紧紧拽着那少年的衣袖,不让他上前一步,而那少年依旧怒目圆瞪,双手握拳,胸口剧烈起伏着。只听那老仆轻叫了声:“三少……”似是哀求。那少年怒道:“你别管我,我有分寸。”那老仆急道:“三少,你不管老夫人伤心了吗?”那少年听了方才叹了口气,两眼的愤怒转为不甘,又定定地朝前望了眼,转身离去。 那老仆早已备了马车,待那少年向里一钻,便挥鞭离去。马车直接出了城,向西蜿蜒地走了几里路,在一户隐秘的小院落前停了下来。少年一越下马,直接走进屋内,当地跪下,口中道:“儿子让母亲担心了。”当下屋里正中端坐着一个妇人,一身缟素,眉头微蹙,却默默不语。一边坐着另一少年,年纪略大些,脸色深沉,亦穿一身素白。他看了那妇人一眼,便问道:“见到你表姐了?”另一个点点头。他又问:“你去想做什么?是抢亲吗?”跪在地上的少年突然抬了头,愤愤然道:“哥,我只是咽不下这口气!我今天只没见到那白老鬼,要不然就同……”还未说完,那妇人就匡地一声咂了手中的杯子,厉声道:“同归于尽吗?你真是出息了,跑到人家大门口去做英雄好汉,去撑一时意气,早知你这样自轻自贱,也不用枉费人家一片苦心保全你,辜负了你九泉下的爹……”说着已哽咽住了。坐在一边的那个少年道:“子离,快和母亲认错。”子离却直直地跪着,咬牙道:“儿子是卤莽了,但儿子没有错,父仇已不共戴天,如今他又巧取豪夺,占人之妻,这等深仇血恨,叫我们怎么罢休!”那妇人气道:“好好,你如今长大了,我也管不动你了,你到你爹和你大哥面前去,要是他们也同意,你就去和那姓白的一起死吧,我全当没你这个儿子!”子离见母亲伤心,虽然气怯,但一脸傲然仍不惟所动,还想再说,却被一边的少年喝住:“够了,家里已经这样了,你还要把母亲气病吗?跪到爹和大哥面前去!”一旁的老仆忙扶起子离,拉扯着把他拖走了。这屋里的另外二人各自坐着也不出声,半晌那妇人方叹了口气,道:“我早知道子离是忍不住的,不过有我们看着料也出不了事,只是可怜了怀凤。”另一少年不语,一双长眼半敛,嘴角透着阴郁。那妇人又道:“子巽,娘知道你比谁都不好受,都藏在心里你是受不住的,你有委屈就去和你爹说吧。”子巽道:“是我疏忽了,我应该早早的就把怀凤娶过来,殷越正这棵墙头草我早知道靠不住,只是不防他还有这手。”韩母冷然道:“谁会想到呢?为求自保连女儿也卖!” 不一会天已黑了,这天的月色很好,似乎浸透在东边厢房,月光射在灵牌上,把几个烫金的字呈现得清清楚楚,一尊上写的是韩公广善,另一尊则是韩子坎。韩子离默默跪在灵位前面,脸上的倔强已然褪去,神色却越发痛楚,他想起七岁那年他拿墨泼在老师的白胡子上,他当时也是不肯认错,还对着四书偷偷扮着鬼脸,叫他父亲看见了,一顿狠打后关进祠堂,那天祠堂里也是一样的月色,只是当时对着许多牌位有点害怕,而现在只剩下凄凉。他想起后来是大哥来接他的,韩子坎神情严肃,眸子却透着温和,他说了句什么,然后自己就哈哈大笑说:“我一点儿也不害怕,叫我对着那白胡子,我情愿在这里玩。”后来韩子坎就敲了下他的脑袋,拿了个装食物的盒子给他,又把自己的披风裹在他身上,嘱咐了几句走了。他说了什么?为什么自己记不起来了?韩子离只觉心中一阵酸楚,仿佛抓住些往昔的记忆就能填满此刻的失落,忽然觉的脸上一道冰凉划过,才发现自己落泪了。身后的门支呀一声开了,进来一个颀长的身影,子离嘴角边还留着泪痕,叫了声:“二哥。”就一下子扑到那身影怀里痛哭起来。韩子巽的手在他背上轻轻拍打着,一下又一下,好似在镇痛疗伤,他沉吟:“子离,你已经长大了,我们身上背负的责任,你懂吗?”韩子离豁地抬头,一双眼睛分外明亮,道:“我明白,报仇血恨,复兴家业。”韩子巽道:“很好,可是你也要明白,真报仇就不能把这两字时时挂在嘴边,如今白令璩大权在握,你要学会忍耐,懂得等待时机。”子离轻轻道:“哥,今天的事是我卤莽了。”子巽微微笑道:“你能这么说就是真的长大了,爹和大哥也能安慰了。”子离擦干了泪,问道:“大嫂好吗?”子巽道:“我让芳儿一直陪着她。”子离点点头,又道:“我今天瞧见凤姐姐了,本来……”又止住不语。子巽道:“本来这个月,我们是要成亲的。”他走至窗边,月光正好洒在他身上,此刻他眼神不再收敛,其中分明地交织着仇恨和愤怒,嘴角却微微向上一翘,似是讥笑:“多么嘲讽!原本是韩广善的儿媳如今却成了白令璩的七姨太。”半晌,他突然转身,在两个牌位前一跪,举起右手道:“我韩子巽在此立誓,有生之年一定不忘杀父弑兄之仇、夺妻之恨,必将尽我所有为韩氏一门讨回血债,苍天在上,父兄为证!” 第3章 殷怀凤正坐着对镜理妆,一回眼瞧见门口有个婆子微微探头,便对采音道:“去瞧瞧什么事?”那婆子却已经进来了,恭谨地道:“七姨太早,我是大夫人派来伺候的,您唤我甘嬷嬷就行了。”说着便要跪下磕头。殷怀凤忙叫丫头搀起来,口中道:“嬷嬷快别如此,您是这里的老人了,我一个晚辈担待不起。”对采音使了个眼色,采音会意,回头开了八宝柜子,拿出两个笔锭如意的锞子,甘嬷嬷却执意不肯收,殷怀凤道:“这原不过是个彩头,嬷嬷留着玩吧,我初来乍倒,这府里的许多规矩还要嬷嬷指点。”甘嬷嬷笑道:“这里合府上下的人都很随和,七姨太放心。”又指着门口的四个丫头道:“这都是太太拨来伺候的,七姨太你看着还满意吗?”殷怀凤微微笑了笑,又命采音散赏,那几个丫头都进来谢了恩,甘嬷嬷瞧见殷怀凤着一身蜜合色小袄,配着玫瑰色的金银鼠比肩褂,眼如水杏,眉山如画,亭亭玉立,不由喜道:“七姨太好俊的模样。”又瞧了瞧外面。怀凤会意,知道是晨省的时辰,便道:“该去给老爷太太请安了。”她这是头一回,生怕迟了失了礼数,便抬脚想出门。谁知门口早有二个婆子等着,笑道:“新姨太别急,现在时辰还早。”怀凤知道她们是专程来接的,说了早必是早的,便也驻足在门前。她回头一瞧,便瞧见自己的住处鲜花烂漫,清幽雅静,一块破旧的木板上刻着“沉香苑”三个字,却是苍劲有力,一看便是名家手笔。她站在这鸟语花香之中,不觉有些怔仲。 彼时进了正屋,才发现屋里已坐满了人,正中端坐一中年男子,身旁坐着一个妇人。怀凤不敢细看,早有丫头拿了垫子来,怀凤便立刻跪下,恭恭敬敬地道:“妾身殷氏怀凤给老爷太太请安。”只见那中年男子忙起身过来亲自搀起,哈哈笑道:“不用多礼。”白令璩瞧见怀凤明艳照人,倒也微微一愣,随即笑意浮起,亲自搀着认识众人。先是大夫人,因刚才已经行过礼了,怀凤只福了福,赵氏神情冷淡,不过对怀凤倒也一笑,递了个红包给她,口中道:“以后这里就是你的家了,吃穿用度只管和你嬷嬷开口,别让自己受委屈,这里的都是你的姐姐,虽说一样,但她们比你早进门,不可缺了礼数,大家相处和睦才是正经,这就是我的话了。”怀凤答是。接着是二姨太,她和赵氏差不多年纪,神情却是十分温和,没有大户人家娇纵之气,她只对怀凤笑了笑,不敢多语。二姨太对面坐着李氏,她站起来拉着怀凤的手细看,对白令璩笑道:“我可要恭喜老爷了,竟收了个天仙在家里,可见老爷福泽不浅,不仅叫天子刮目相看,连月老也要横一脚呢。”白令璩笑道:“就是你的话最多。”又对怀凤道:“这是你三姐姐。”怀凤便福了福,李氏忙拉起,口中道:“自家姐妹,何苦来那么多虚礼。”李氏身旁的那位妇人却很安静,她容貌也美,却不夺目,她站起来对怀凤微微一笑,怀凤见她面色雪白,身形怯弱,神情略有些不自然,只听白令璩道:“这是你五姨太,姓梅。”怀凤照样行礼,梅氏轻声道:“妹妹多礼了。”怀凤瞧见梅氏身旁还坐了个小女孩,模样清秀,神情却漫不经心。梅氏道:“这是小女。”白令璩似乎想起什么,便问:“大爷和二爷呢?”门口的丫头道:“在外面候着呢,没有老爷的话不敢进来。”白令璩便道:“叫他们进来见过新姨娘。”又对李氏道:“把岚之也带过来吧。”方让小辈们行了礼。怀凤忙将两个小女孩搀起,一人给了个红包。岚之大约十三四岁,容貌和李氏很像,接了红包后对怀凤一笑,便坐回李氏身边。梅氏之女年龄还小些,却在细细打量怀凤,不一会儿对白令璩笑道:“爹,这个姨娘的年纪倒可做我姐姐。”此话一出,一时间屋里十分尴尬,但谁也不敢出声,只李氏微微含着笑意,梅氏却慌忙走过来拉起那女孩,口中道:“络之,不许乱说。” 白令璩瞪了她母女二人一眼,梅氏的神情越发慌乱。这时赵氏道:“惠儿,你怎么教四姑娘的,越大越没规矩,四儿,这是你七姨娘,不可乱叫。”白令璩对那女孩道:“还不快叫姨娘!”一边说一边看了怀凤一眼,只见怀凤神色如常,正看着白络之,白络之也不以为然,叫了声姨娘就跟着梅氏坐回原位。屋内渐渐又热闹起来,各自套些家乡风俗。怀凤昨夜不敢独自先睡,只在床上翻来覆去,直到清晨方打了个盹,故此刻疲倦异常,只是脸上也不好露出,随着大家说着场面话,到午饭前才散。 一转眼怀凤进府已两月有余,她平日无甚好做,除了晨昏定省外,就在沉香苑里看书写字或做些针黹刺绣。这一日午后,怀凤正拿着本书在看,忽来了个婆子,怀凤认得是赵氏那边的人,便问什么事。那婆子笑道:“才刚宫里有人派赏过来,太太分了让我给各房送来。”怀凤道了谢,又问:“你们太太在做什么呢?”婆子道:“在歇午觉呢,恐怕晚上还要忙六姨太回来的事。”怀凤一楞,问:“六姨太要回来了吗?”婆子回道:“听说六姨太已经大好了,最迟这个月底就搬回来了。”怀凤哦了一声,又给了那婆子一吊钱便打发她去了。恰好这时丫头明慧进来,怀凤就随口问问:“六姨太得的是什么病?”明慧是从小便在白府服侍的,听说便抿嘴一笑:“只怕是心病。”她见怀凤瞧着她,又道:“七姨太您没来这以前六姨太可是最得宠的,她一听说老爷要娶你就立刻病了,你说这不是心病是什么?”怀凤不作声,一旁的采音便道:“老爷最宠六姨太吗?我瞧老爷很喜欢三姨太。”明慧悄悄笑道:“喜欢是喜欢,不过俗话说的好:岁月不饶人。”她瞧见怀凤神色黯然,忙赔笑道:“七姨太您放心,老爷对你这么上心,就算六姨太回来也排不过您的次序去。”采音拧了她一下,笑道:“瞎嚷嚷什么,叫人听见了倒抱怨我们轻狂。”明慧摇着头说:“怕什么,前儿中秋那晚老爷还来我们这里呢,连大太太那儿都不去,合府上下谁看不出来我们七姨太的地位。”怀凤突然问:“以前的四姨太是怎么死的?”明慧冷不防被问了这么句,就回道:“提起这四姨太就可惜了,那时我还小,听说也是个大美人,老爷欢喜得不得了,只可惜没福,进府不到两年就一病死了。”她既打开了话题便越性说下去:“其实老爷这些太太里最有福的还是三姨太,有儿有女,老爷又喜欢二少爷。大太太虽好,但没有儿子,只好把自己的丫头给了老爷,你瞧云姨娘多可怜,顶了个名分却做丫头的事情,再者老爷也不看重大少爷。那六姨太虽美,但脾气性格却差,你瞧老爷最近都不提她了,如今只好急急忙忙地自个儿回来。”怀凤闭着眼睛,似听非听,采音又问:“那五姨太呢?”明慧道:“那更别提了,老爷从不拿正眼瞧她,同云姨太一样可怜。”这时怀凤叹了口气,道:“我乏了,想歇歇,你们出去说吧。”采音明慧忙止了话,伺候了怀凤歪在大躺椅上便掩了门出去了。 这天晚上怀凤把从家里带来的琴拿了出来,又让采音点了香泡了清茶,自己坐在窗下案前抚琴。她虽是抚琴,实则是平定心绪,想着自己在白府前途漫漫,百无聊赖,不仅悲从中来。不过几个月前,她去舅舅家做客的时候,子离还打趣地喊她嫂子,她当时飞红了一张脸,转身想走,却看见子巽正在背后含笑望她,当时自己又羞又气,如今想起来却是辛酸的甜蜜。她正感叹着,忽听着外面道:“三姑娘四姑娘来了。”她正要起身,就看见两人已走进来了。怀凤忙唤人倒茶,又摆上了水果盘子。白岚之拦道:“姨娘快别忙了,我们只来问安,再说晚上我们也不吃这些生冷东西。”怀凤便罢了。白岚之笑道:“今天母亲和我说有几天没瞧见姨娘你了,便打发了我来问安,才到门口就瞧见四妹妹也往这里来呢。”白络之是头一回来,正抬头瞧着墙上的两副字,听说便道:“我远远地听见琴音了,是姨娘你在弹吗?”怀凤含笑答是。白岚之只觉室内清音余绕,暗香浮动,看见窗下案上放着一把琴,边上整整齐齐地磊着几部书并一盆素菊,便走过去道:“好精致的一把琴。”白络之也看了一眼,道:“三姐姐不也是行家吗,何不弹一首?”白岚之笑道:“姨娘可是本省出名的才女,我何苦班门弄斧。”怀凤笑道:“才女不过是虚名,不知有多少人都被虚名蒙蔽了呢!”白岚之不语。一旁的白络之便笑道:“前儿还有人说三姐姐是我们白家的女状元呢,不知是不是也担了个虚名呢?”白岚之嗔道:“就你这张嘴促狭,平日里不学无术,流言蜚语倒记的快。”三人说笑了一回便散了。 过了几日怀凤正在院里的池塘里喂鱼,抬头看见白络之又来了,不过这次只她一人。她不过十二岁年纪,身量还未长足,一头乌漆的头发扎成两条小辫搭在胸前,衬着清秀的小脸越发白皙,一对乌黑的眸子十分灵动,让怀凤想起第一次见她时候她就是转着这么双眼睛对白令璩说她像她姐姐,怀凤不觉莞尔,便问道:“怎么有空过来?”络之道:“母亲让我过来请安。”便看着池塘里的鱼,叫道:“哎呀,这里的鱼好胖,比前面院子的大多了。”怀凤笑道:“成天有人在喂,不胖才怪。”络之道:“怪不得,前面的池塘都有嬷嬷看着,连拈根草都不让。”怀凤问道:“你是主子,她们敢不让?”络之微微笑道:“若是三姐姐,她们当然不敢,不过如果是我,那就说不定了。”怀凤会意,便把鱼食递给她,笑道:“那你在我喂吧,只别把它们撑死了。”络之那天便在沉香苑待到吃晚饭,梅氏派了人来接才走的。之后她就常来,只说来给姨娘请安,有几次还在那吃晚饭。怀凤为人沉静,络之也不是热情之人,不过二人相处倒还和睦。无聊之时,怀凤便教她诗词歌赋,琴棋书画。白府也请师傅教授各房小姐功课,不过自从有了怀凤她便不去上课。络之秉性聪颖,就是不肯用功,不过对绘画倒还情有独钟,肯花工夫练习。怀凤发现后笑道:“你还真会揭吾之短,别的都还好说,只这画技我是一般。”络之笑道:“就是一般,教我也绰绰有余。”怀凤笑道:“罢了,我还是藏拙吧,你另谋高就。”又想教她抚琴,她自己琴技一流,便起了育才之心,谁知络之只肯听她弹,却不肯用心学,一月下来毫无长进。怀凤便气道:“朽木不可雕也。”络之嘻嘻笑道:“各有所长而已。你弹我听,我们各司其位,我若越界,终是勉为其难。”怀凤便批胡说,道:“实话说吧,为什么不好好学?”络之道:“手会疼。”怀凤嗤得一声笑出来,不妨一口茶呛在那里。 第4章 展转已入深秋,谁知圣上龙体又贵恙,这一次来势汹汹,震动了朝野上下。陈公是二朝元老,德高望重,他虽病着,还是出来主持大局。这一日他和白令璩等几个大臣议了事,便由幕僚扶着回到暖阁里。不一会有人报:“屈将军来了。”屈进是他的学生,因头生得特别大,便得屈大头一名。他性情豪放,骁勇善战,深受圣上赏识。陈公谴退了外人,只在藤条椅上歪着,神色疲倦。屈进不敢支声,半晌陈公方叹了口气,道:“各怀鬼胎。”当今圣上并未立储,如今一病,储位之争自然浮上水面。屈进道:“老师看不出皇上到底属意谁吗?”陈公冷笑:“刚才那批人十有八九是来探老夫口风的,一个个精打细算,生恐押错了宝。”屈进坦然道:“他们为求自包,这也自然。”陈公看了他一眼,笑道:“你的心倒公正,就你看储位会给谁呢?”屈进想了想道:“学生拙见,学生认为三皇子和八皇子都有可能。而前些日子皇上重用白令璩,会不会属意三皇子呢?”陈公笑问:“何以见得?”屈进道:“三皇子是白皇后抚养成人的,就如亲生母子一般,白令璩和他更以母舅相称,而此时皇上对白家又格外优容,这不是暗示吗?”陈公缓缓道:“你也会说犹如亲生,犹如亲生,但实则不是,三皇子的生母只是内廷侍女,已故皇后可以宽容大度抚养皇子,当今圣上在择储上却不得不斤斤计较。”屈进道:“可是八皇子的生母出身也不高贵,若按尊卑排序,要属德妃所出的……”陈公笑着摆摆手,道:“十一皇子还不到十岁,进儿啊,你想皇上在对待韩黄一案上为何毫不留情呢?黄津贪污舞弊,结党营私,的确该杀;可韩广善只是包庇罪,他享有善名,与黄津又是同科出身,一时心软替他隐瞒,倒也其情可勉,却叫白老鬼拿来大做文章,以至断头抄家,当时我也心痛皇上杀伐太狠,现在回想倒意味深长。”屈进皱眉道:“学生不明白,尤其是皇上为何抬举白令璩,此人太阴险,不堪重用,就算是为了三皇子也不必杀掉韩广善。”陈公笑道:“你忘了皇上最恨外戚弄权,若圣上真想让三皇子上位,必不会让其与白府过从甚密,看来白老鬼也明白这点,我瞧他也没把注下在三皇子身上。”屈进不语。陈公知道这些阴沉的政权谋划于他不合,便不再说下去。 片刻后屈进离去,陈公便唤了张保才来,对他道:“你去西郊看看,别声张。”张保才应了一声就去了。他先去库房里拿了些东西,就架着一辆半新的马车从后门离去。到了西郊外的小院落内就看见一个老仆正在拔草,他迎上前去微笑道:“快入冬了,你拔它做什么,横竖它自己会谢。”那老仆道:“少爷让我把这块土腾挪出来,围个栏杆养些家禽。”张保才笑道:“你家少爷倒是准备在这长住了。”回头便从马车上搬东西下来,不过一些衣物日用品,最后又拿了几坛好酒,道:“这可是老哥我藏了好几年的。”才说完就有声音道:“什么好东西让你藏了好几年?”张保才忙笑道:“原来二爷在家。”韩子巽道:“你家老爷身体好吗?”张保才笑道:“最近倒硬朗了不少,还忙着朝事呢。”子巽恩了一声,又笑道:“这些天我倒在学着务农,往后可要自给自足了。”又对老仆道:“去告诉老夫人一声,说我和张叔叔在书房说话。”便领着张保才进去了。 张保才在书房里待了一顿饭的工夫便告辞了,子巽坐在书房里拿一本书看,只是良久未曾翻动一页。书桌上放着一盘围棋,黑白二子正斗得不相上下。他合上书,一只手指慢慢地在桌上画圈,眼睛似是看着手,又似什么都没看。他的脸色越来越阴沉,眼睛里闪过一丝哀凉,却稍纵即逝。渐渐嘴角浮出一丝笑意,却是苦笑。此刻以近黄昏,夕阳透着窗上的碧纱射进来,却叫窗外的几杆翠竹档住了,书房的地上尽是竹影,风一吹过,竹影便晃动起来,晃得整个屋子忽明忽暗。他听到隔壁屋子说话的声音,便知道子离回来了。不一会声音轻下来,门支地一声,子离已经走进来了。他便沉声问:“又去哪里逛了?”子离道:“去西郊草场跑马了,一时忘了时间。”子巽道:“你是生恐人家找不到你是吧,非得去那种地方招摇。”子离笑道:“怕什么,现在还有谁顾的到我们,他们都忙着改朝换代呢,我也趁着机会疏疏胫骨。”子巽皱眉道:“你是不是和谁打架了?”子离道没有。子巽笑道:“你说谎的本事还没到家呢,进来半天这么规矩,是不是伤到腿了?”子离方哎呦了一声,一下子歪在椅子上,口中道:“早知瞒不过,我就不装了。”子巽便走过来瞧,原来是伤了腰,亏他刚才还站得笔直。子巽便去拿了药油来给他擦,子离就趴着告诉他原由,时不时还痛叫两声给他听。原来今天在西郊草场和人赛马,碰到树枝给跌下来的。子离道:“哥,你不知那小子有多猖狂呢,一副舍我取谁的样子,我就说真工夫得在马背上试,他也二话没说就上了马,谁知后来跑出了草场进了树林,我就给摔下来了。”子巽道:“那人是谁?你清楚吗?”子离道:“以前没见过,像是富家子弟,后面还藏着好几个保镖呢,他还当我没瞧见,说自己是路经此处,踏兴而来,我原来不想理他,谁叫他身边的一群人这么狂妄呢,说什么公子骑术天下第一,我忍不住笑出来,叫他听见了,他问我你笑什么,我……反正后来我们就吵了起来,最后就上马了。”子巽不语,一会又问:“那人多大年纪?”子离道:“和我差不多吧。”子巽又问:“他知道你是谁吗?你知道他是谁吗?”子离道:“倒忘了问彼此姓名,不过也没什么要紧的。”子巽拍了下他的头,口中骂道:“你把脖子给摔断了,那时才要紧呢。” 子离休息了几日便又去西郊草场了,他远远得瞧见一个翩翩公子等在树下,清朗俊雅,口角含笑,便笑道:“你倒信守承诺。”那公子笑道:“上回胜负未分,心有不甘。”子离道:“上次是你赢了,不过这次你就妄想。”那公子一笑,二人翻身上马,踏尘飞去。他们各自手持一枪,空出一手控绳,在空中铮铮地打了起来。那公子身形伶俐,十余招下来不落下风,几里之后才渐渐不持,而子离自小练就骑术,又爱舞刀弄枪,在马背上可谓如鱼得水。最终是子离先到终点,那公子哈哈一笑:“果然技高一筹。”子离翻身下马,环顾四周,道:“夷,今天怎么没有那帮跟屁虫?”那公子道:“君子之交贵在坦诚,你只身前来,我怎能左呼右唤?”子离心中高兴,刚才打斗时已有知交之意,便道:“在下子离,还没请教大名?”那公子似乎微微一楞,旋即道:“容素。”自那之后,间隔十几天二人便会相约去西郊草场,时而赛马,时而吃酒。二人年纪相当,言语投契,子离虽然心怀坦荡,但对家事却只字不提,容素倒也并不在意。 转眼就要过年了,这一日容素拉着子离说要去拜访一个人。二人经过市集向南到了条冷僻的胡同。子离瞧见胡同冷落荒凉,便笑道:“难不成你要拜访什么法外高人?”容素道:“我可是景仰了这位先生很久了,一直想拜师,屡屡被他拒之门外。”子离便问是谁。容素道:“东方曜。”子离哑然失笑,问道:“此人是否高约五尺二丈,面孔蜡黄,额头突出,蓄着山羊胡。”容素惊道:“正是此人,你如何知道?”子离笑道:“罢罢,想不到你还有如此嗜好,他的经事治国论最让我头痛。”容素越发惊讶:“原来你竟和他相识,我屡屡求教受挫,原来他竟赏识你。”子离大笑:“我在他嘴里曾是玩劣不堪,桀骜难训,只怕他如今提起我来还要横眉怒目呢。不过你如真心想拜师,我倒有个人真可帮你。”容素忙问是谁。子离道:“我们先进去瞧瞧吧,想不到他又回京了。”便以手叩门。一老妪开了门问找谁,子离便道:“我们是来拜访东方先生的。”那老妪道:“东方先生现在不会客,二位请回吧。”子离便撤下身上的一块玉佩,笑道:“你拿这个去与他瞧,说韩子离乞见。”老妪将信将疑地看了他二人一眼,转身进去了,不一会出来开了门,道:“老爷请。”二人进了门,只见庭院冷落,寂寂无声,不像有人居住。那老妪让他二人进了偏厅,容素看见一个老者与一年轻男子正在对棋,那老者与子离形容的一样,只是更苍老一些,那男子背对着他们,身影十分挺拔,二人全神贯注对着棋,并未朝他们看一眼。这时子离却大叫:“二哥。” 子巽回头,目光却越过了子离,凝视着他身后。容素上前朝那位老者恭敬地作揖:“东方先生。”东方曜朝他点点头算是回礼。子离却行了大礼,口中唤道:“老师,不肖弟子请罪来了。”他虽如是说,口角却含笑。东方曜眼睛看棋,口中道:“起来吧,老夫什么也没教会你,可担不起你的大礼。”子离却跪着,笑道:“是学生愚钝,老师一番苦心从不曾领会,叫老师伤心了。”说着便磕了三下头,又道:“好在还有二哥代我敬孝,老师就看在二哥的份上,再赏学生一顿骂吧。”东方曜慢慢将眼睛转向他,含笑道:“以后骂你的大有人在。”又把眼睛转向容素,道:“容公子真是执着之人。”容素道:“古人可以程门立雪,在下这不算什么。”东方曜问道:“公子几番造访,想让老夫教授何事呢?”容素道:“天下事。”东方曜呵呵笑道:“老夫是过时之人,世俗之事实不想招惹太多,况如今粗茶淡饭,俗欲之心早淡,恐怕对不住容公子的抱负。”容素看了子巽一眼,道:“东方先生既然想避世,为何又回到是非之地呢?”东方曜微微笑道:“为了缅怀故人。”容素便不再语。子离想开口,却瞧了一眼子巽,子巽只看着棋盘,若有所思,子离便默默无语。不一会东方曜笑道:“青出于蓝,子巽啊,这盘我怕是要输了。”子巽笑道:“是老师的求胜之心淡了,步步只是以和为贵。”东方曜道:“我老了,明白这世上种种的计较不过是浮华烟云,输赢只是虚名。”他又看着容素,笑道:“公子不是想请教天下事吗?这就是老夫对天下事的看法。”容素到底年轻,一脸不以为然。东方曜又笑道:“怕是不对公子胃口,其实公子想求教的事并不需老夫教授,也不写在任何书本上,公子若想明白个所以然,亲身经历便可。”容素恭谨回道:“谢谢先生提点。” 子离与容素别了东方曜,走了几步二人都不语,容素忽然道:“后日西郊猎场,是否不见不散?”子离似乎有许多话要问,但只回答了一句:“是。”容素十分高兴,道:“今日种种今后我一定给你个满意的解释,感谢你的信任。”子离一笑,二人就此别过。容素见子离走远,自己折回原路,依旧来到原先的胡同,这次却不走到东方曜那里,只在旧巷里停住,一个男子等在那里,见到他来便单腿跪下去,口中道:“罪臣韩广善之子韩子巽参见八皇子。”
下载地址:
点击下载TX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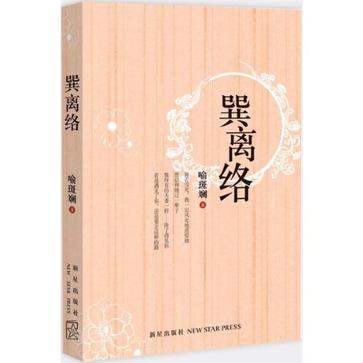 作者:喻斑斓(现代)
作者:喻斑斓(现代)